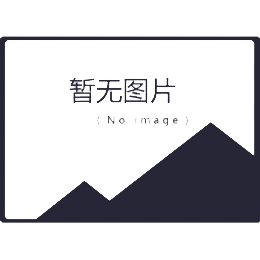短篇小说:驶向前方

作者舒生,一直在跋涉的文字匠,终身写作践行者,自媒体〖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主编,苏格拉底和王阳明思想学说研究者。
作者的话大学时期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段淳朴而懵懂的感情,故事背景以我的家乡为原型,有我童年生活的影子。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短篇,希望你也喜欢。共18000多字。旧文更新,主要是为了留作纪念。
驶向前方
一
“李昕考上省城一中了。”
这喜讯普一出来就在良村引起巨大轰动。虽然从小学六年级起四乡八邻的人们便把他当作最优秀的学生看待,但大家都没想到他竟然优秀到能考上省城一中。
良村是一个落后的村子,在此之前从没有人上过省城一中。以前一些优秀的孩子能考上县里第一流的中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他们哪敢奢望有天能到全省最好的高中就读。但不管村里人如何感觉惊讶,李昕就是考上省城一中了。
天啦,居然是省城一中。父母们想起来心便发抖,这太了不得了。要是他们的儿子也这样风光就好了。父母们都羡慕他母亲有这样一个儿子。
然而,当李昕捧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时,却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他随便睃一眼这张让他名闻四乡的通知书,转身递给了他母亲,也不看她一眼就走出有些昏暗的屋子。
他母亲小时念过两年书,不像其他妇女一样是彻骨的文盲,在有些炙人的太阳底下他想象着他母亲读完通知书后热泪盈眶的情形。他太了解母亲了,这个以前常遭酗酒的父亲面包毒打、自尊心极强的女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是她唯一的儿子,是她唯一的骄傲。每当听人们夸起他这个争气的儿子她就热泪盈眶。
李昕自己最清楚母亲并不娇惯他,相反,她在生活中更像一位严父而非慈母。纵然她也如天底下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她从不逼迫儿子做任何不愿做的事。她只是尽量在生活中开异他,表达她理想的儿子的模样,但并不给他施压。所以,即使在儿子一至五年级成绩平平,她仍没责怪过他。但到了六年级,母亲因受不了父亲的毒打选择了外出打工。
她南下打工约一个月,这段时间里她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家里就剩下父子俩。父亲是个粗人,根本料理不了家里的事。所以,这段时间他们连吃的饭都常是发霉的。就在那时,他异常怀念母亲在家的日子。并且感到愧对母亲,便开始勤奋地学习,幸运的是,不久她回来了。但她要和男人搭成一个协议,即他在家不能超过一月,男人在这个月也深味到家里没有她的落魄样,虽不大情愿,但仍坚持要履行这个协议。以后男人基本不在家了。
李昕上初中这几年男人都在外打工,只在过年或农忙时节回来住一段时间,又识趣地走了。李昕打小对父亲的印象不深,父亲在外这几年,他有时甚至忘了他还有父亲,要说,他并不恨这个男人。李昕有时想到这个父亲在儿子心中竟如此的无关紧要,便可怜起这个男人来。
没有男人的日子他们母子俩过得很清静。总之,他对父亲没有感情。现在他父亲去了外省,李昕只从母亲口中了解到他父亲只言片语的消息。关于他父亲,就这样。
他现在已没有心思想家里的事了。他觉得想这些没有用,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
况且,英子又来找他了。
二
“在这里发什么呆,大人物?”
她冲上来向他喊。他显然没有心思理会她的话,但他仔细打量着她。还是老样子——头发泛黄、用红头绳扎成马尾辩,面色红润,眼珠子像稻田里青蛙的眼睛那般饱满,闪动着如两颗太阳底下的晶珠,胸脯挺挺的,穿着那件似乎常穿常新的浅红色的绣花圆领衬衫,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马裤,小脚上一双塑胶拖鞋。他把她上下打量完,便傻傻地冲她笑。
她被他的行为搞蒙了。但也不发话,只用直勾勾的眼光回敬他直勾勾的眼光。“这阳光真令人恼火,我们走吧。”大约对峙了十来秒,李昕突然打断了沉默。走就走,她也不问去哪里。
李昕说不说她都知道他要去哪里。她不但不问,还装出很深沉的样子,仿佛他们正去完成一件机密任务。
他们是要去捉螃蟹。不过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绝不让第三者插足。
每次去捉螃蟹他们都从张家口开始捉起。张家口是他们之前上学的必经之地。沟壑从这里穿过。两旁怪石林立,沟水至清,他们喜欢从这里开始,每次到这里来,英子何时和他在一起的疑问总在他头脑中一闪而过。
他知道他们是在六年级(下)的某个炎热的日子里同座一桌的,但他记不清到底是哪天,为此他常自责。但他没有告诉她这种愧疚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心理想着得到安慰就行了。
阳光蛰得他们全身上下痒痒的。离张家口还有一段距离,英子已经抱怨起道旁的包谷叶和杂草来。她露出的小腿在谷叶、草叶的婆娑中难痒无比。她只好用手抱住小腿肚蹒跚地走。终于,她不走了,蹴在路中央,头在冒汗。他回头盯着她,他知道他又要背她了。
“我是不是很残酷啊!这大热天还要你背。”她在背上若无其事地说。见他不说话,她也沉默了。她的眼珠子机灵地转动着,她在看路上有没有人。她不好意思别人在路上看见他背她。
到张家口时,他汗如雨水,不断滚过腮颊。他把她轻轻放到一块石板上,喘着粗气,这时她有了一点点的“侧隐之心”。但她止不住“扑扑”地掩面而笑。她觉得自己太过残忍,但她就是喜欢这种残忍。
他和她在一起时,她从不把他当“大人物”来看。相反,她想奚落他,她尽量把他和这条朴实的路融合起来。是的,他就是这条路,不管它延向何方我都要把它踩在脚下。并且我要天天踩……
她现在恢复了常态,但仍莫名其妙地打量着他。她发觉他脸上有些微的变化,似乎藏有某种深意,但她一时想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倏地她脑中又闪现了干燥的灰白色的路面的形象,这是一种因承受了阳光过多恩赐而扭曲的焦灼形象。他蹲下去掬水来洗脸。他有股洗洁一切的冲动。
她也蹲下来,但并不洗脸,水流晃出两个人的影子,她极力想在水中分辨清他的影子。但水流湍急,只有两个模糊的影子晃来晃去。她有些失望。这时他洗完了脸直盯着她。他的心有点乱,他感觉心底有什么使他措手不及,为此,他真想把他的心——他常想心是什么模样——挖出来清洗一翻。
中午时分的阳光过分耀眼。人们承受不起这样的阳光的爱抚,都在屋里躲荫凉。但土地多的人家都会把陈豆旧谷从楼檐上抬下来翻晒一番。父母懒的人家便让他们的孩子看管。孩子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大声吆喝一陈,就去躲荫凉了。这还是乖孩子的做法。
若遇上个忤逆、好四处游玩的孩子,那吃粮的牲口就可趁此饱餐一顿。获益的还有各种飞禽走兽。这可真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世风。可眼下倒使英子为难起来。她突然想到她爸妈都去赶集去了。需要她翻晒粮食。她可是村里公认的乖娃娃,虽然她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她心里踟蹰不定。在他们沉默的少顷,她似乎听到鸡呀鸭呀在坝子里啄粮食时“嚏嚏”的声音。然而当他泰然但坚定地说“出发”时,她又一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
夏天,只要是干晌的日子,水沟里的水总是清澈透明的,除非是孩子们刚在里面捉过螃蟹不久。阳光炙热,别的孩子们都不愿在这时出来。确实,对于深谙自然之道的人来说,此时不但热,更重要的是遭到太阳烘烤后皮肤会被晒黝黑。男孩情有可原,若是女孩也这样疯狂在太阳底下,怎了得?为此,英子觉得自己不是个乖娃娃。你仔细看时,便会发现她脸上有一些阳光长期晒成的黑斑。
他们往深沟里走去,只听见拖鞋在水里“吧哒吧哒”的响动。他们来到一处水深至膝盖,上方笼罩着一大笼带刺的蔓藤的水沟里。阳光透过蔓藤在凉悠悠的水里形成离奇的金边。她感到害怕,她她怕里面有水蛇,或那种丑陋得可怕的水虫。她怕它们从她的脚板下手,像蚂蝗一样在脚板心里吸血。
想到这她就怕得要命,紧紧挽住他,生怕失掉了这唯一的依靠。“你先上岸,坐在石板上等我。我要捉蟹。”
“都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祸害……”她极不情愿地要丢开他上了岸。
他开始在水里四处摸,这他太有经验了。
蟹常蛰居在哪种水石块之下,它们一般躲在石块的哪个方向,会藏多深,它们怎样保护自己等。他闭上眼都能捉到它们。他自小就喜欢捉蟹。他觉得蟹是一种极其可爱的水生物。
每当捉到一只较大的螃蟹时,他便会笑眯眯的抠住蟹壳,用另一只手在蟹身上摸来摸去。他最喜欢它们的眼睛啦。他喜欢看它们那两只如发霉变黑的米粒一样的眼睛。你把它捉在手里,两只眼便会从眼眶中弹出来,直白地看着你,仿佛在说:“嘿,小子,玩够没,玩够了就把我放了,俺受不了了。俺想家了。”
这时他心里也跟它讲起话来:“哼,想我放你,没门!我真想掴你几个耳光,你这个滑头!”
蟹一看,不对,这招骗不了他。等我想一下,哦,有了。它兀地关上了它的眼睛。它这样做有几个意思:
一、我玩够了,没心情跟你逗下去了。二、你把我折腾够了,你太让我伤心了。三、再不放我,我就要死了。果然,此计一出,他很给面子,放走了它。
若是每次都把捉到的蟹放锅里煎了吃,那这沟里的蟹怕早就绝了种。小时侯他把捉到的蟹放进油锅里炸来吃两次后,便没再吃过蟹肉。死蟹那股腥味让他受不了,况且看到那么可爱的蟹死去,他更是一千个不愿。直到现在他仍对蟹情有独钟。
当他看到沟边有些蟹的尸体时他便痛惜不已。看到同伴们蹂躏蟹,他会一改常态地呵斥他们。为此,同伴们都不愿同他一起捉蟹。他们觉得他这种癖好不可思议。所以她没跟他一起时,他只能一人形单影只地捉蟹。
那是在他们被老师调至同一桌后的当天下午,他们一起回家。天气闷热,行至张家口时,他毫不客气地跟她说他要从沟里回去,说完便要走。却不想英子竟一声不响地跟他在身后。她的举动让他感到惊诧,便问其故。她也冷冷地说她喜欢螃蟹,但讨厌那些男孩把它们捉到后进行五马分尸,他们支解这些可爱的生物让她感到恶心。
末了她问他是不是也像其他男孩一样对待捉到的蟹。他笑而不答,沉默了一阵才说你走着瞧吧。说完便开始捉蟹。
其实他满心欢喜,他没想到还有人同他一样对蟹有同样的兴致。那时他十二岁,已经感到了孤单。除了捉蟹外,他都能与其他男孩扭成一团。而且他本人也确实喜欢他们身上的野蛮气息,但他觉得一种近乎天然的孤独阻止他与他们近一步交往,他对他们的行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满。所以,他常常一个人。
一个人去割草,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去山上玩,一个人捉蟹,一个人沉思。
没与他们一起他反尔觉得轻松快乐,孤单的快乐。现在小女孩跟在他身后让他局促不安。他不能把全幅精力投在捉蟹上。所以一路上被蟹蛰了几次,他的右中指都被蛰出血了。痛还不说,更恼火的是他觉得他在这个小女孩面前丢了脸,让他很没面子。
事实上她一直微笑着看他,她觉得他笨拙得可爱,对他的伤,她很心疼,但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她以前跟别的男孩一起从没在他们被蛰时安慰过他们,是对他们的憎恨遏杀了她对他们的悲悯之心。
当他们行至水沟的尽头,重踏上回家的路时,他突然对她说:“英子,我其实很有经验的。”
“嗯。”她吱唔一声便哧哧地笑了。他感到无地自容。
“那我走啦。”他扔完话便跑。
她在后面喊道,“下次捉蟹时叫上我啊!”
他跑得飞快,感觉她最后的话像箭一样钻进他耳朵里。那天晚上他早早地上了床。他先是心里骂了她一通,夜深后,他竭力控制思绪不去想她。但他感觉她的影子老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如噩梦般挥之不去。鸡鸣第一次时,他才浑浑噩噩地睡去。清晨他又在睡梦中惊醒。他梦到她了。
他仔细回忆了一遍,想起来了。她在梦中只有一张干净的脸,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一爽鼓鼓的眼睛噙满晶莹的水。他们仿佛在一个林子里,但他无法确定。因梦中他只看到她脸上方的林子时隐时现。一阵惊恐之后他彻底清醒过来。
父亲没在家,母亲煮好了粥和鸡蛋,她把它们放在松柏做成的未漆的木方桌上等着他来吃,他眼圈布满血丝,睡眼惺忪。他极力在母亲面前掩饰他萎靡的窘相。“昕,昨晚学得太累了吗?”
“嗯,有点,不过过会就好了。这两天学的知识有些难,现在我不想吃东西,你自己吃吧,我上学去了。”他提着书包便往外走,母亲看着他急冲冲走出去的背影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他在上学的路上心理极其烦躁。他不知道怎样面对那个一直嘲笑他的女孩,现在他有点怕见着她。他心理一直盘算着他们见面时怎样面对她。他想象着她又像昨天那样嘲笑他,用同样的眼神奚落他,把他当成一个窝囊废。
这时天边一朵黑云遮住了初升的太阳,大地显得有点暗。包谷林和路旁的杂草熔光焕发,生机勃勃,它们显然是在美美地睡一觉后自然而然地醒过来的,但他一路上都没看它们一眼。
他到教室时还不到7:30,离上课时间还早,同学们都还没到。教室空得让他有点难受,他摅摅自己的思路,准备到走廊上晨读。他没想到刚至走廊,那个令他尴尬的女孩正迎面向他走来。
我是回教室呢,还是继续在这里?她简直是个鬼……难道是我产生幻觉了吗?不,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她快到我眼前了。我该怎么办?继续读书还是……他最后决定不逃,他就要呆在原处,若无其事地读他的《日出》。
当她从他身旁经过时,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如洪钟巨响,还用余光瞟她。他又看到了她脸上挂着与昨天同样的嘲笑。他感觉自己完全被暴露了,赤裸裸地摆在她面前。什么都逃不过她的五指山。
他们才成为同桌,但昨天以前他并不关注她。她虽可爱,但相貌平平。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他看到她与其他男孩一起时的心理,使他对她有所不满),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不必要的话,他都不会看她一眼。有的男孩却衷情于她,她的微笑在他们心中很有影响力。
他已经读了五遍《日出》,他自己都感觉麻木了。抬起头来舒舒心。哇,她怎么……嗯,她在他读第四遍时就在他身边,她静静的看着他,仿佛他的书声就是一道香喷喷的菜让她嘴馋。
“你读得很认真啰”。她又在嘲笑我。
“我向来如此,你不读吗?你个懒鬼。”
“我并不喜欢读书,我宁愿做作业也不读书。”
“那课本上要求背的段落。你怎么办?”
“不背呗。我不是读书的料。我跟你不一样”
“你厉害。”
“我宁愿看日出也不学习。爸妈都说我可以不用努力学习。他们常对我说要给我找个好人家呢。我倒是不感兴趣。”她笑容满面地说。
他注意到她的眼圈也布满了血丝,他从她水晶般的眼里看到一丝淡淡的忧悒。
“我倒是希望妈妈赶快给我找对象呢,那样我就可以带着她满山遍野游逛了。”他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点的真诚,便也想抒发一下心中的情感。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最适合你要求的啦,不过你妈妈才不会给你找,她要你好好读书,我爸妈都说你妈妈是一位很奇怪的妈妈。”
“奇怪?”
“嗯,你是一个奇怪的儿子,她是一位奇怪的妈妈。不知你有没有奇怪的爸爸?”
“我又不是畸型儿,我妈妈就更不奇怪了,她只是比你妈妈多识了几个字。”
“哼,不奇怪,她只要一个独生子,生活那么难过还支持你读书,我们都不明白咯。你说读书有什么用?”
“多着呢,是你自己懒,给自己不想学找借口罢了。”
“懒,人们都说我很勤快呢。我们六兄妹中我最勤快,家里活多由我来做。”
“谁信……”他找不了话说了。想就这样支唔过去。同时,他觉得她的微笑不那么具有嘲讽意味了。他甚至感觉她有些可爱。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涌向学校,他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讲话了。便嗫嚅着回到教室。
这次谈话以后他开始关注她了。他对她的态度也逐渐友好。他自己也觉得这种转变很是唐突。以后他也想过她的嘲弄的微笑。但那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更多时候他对她抱有一种茫然的心态。他不知道他到底对她有何程度的好感。这样想着,另一种恐惧占据了他的心头。
一种对未来不确切的恐怖使他的心不能够安分下来。但这时起,他更努力地学习。近乎疯狂地学习。也就从那时起,每次去捉螃蟹他们都在一起。即使是寒冷的冬天,沟里结了冰或干涸断流时,他们都爱从水沟里走回家去。
回忆使他头晕。他在这一处水沟里呆得太久,不像他一贯的作风。他发觉他今天又重新体验到他们第一次一起捉蟹时那种局促不安的心态。水没过了他的膝盖,他绾至大腿的脚角都被打湿了。凉水浸到他白嫩的大腿上,他感到那种寒凉正向他的腿骨浸去。
他摸的是以前摸过许多次的一块大石板。这样的大石并非四四方方地贴在水底,石板的底部凸凹不平,手臂在这个凹糟里仍有移动的空间。他使劲把手臂往里面伸,但仍不能穷尽石洞,最大的一类蟹一般都藏在这样的石块下,并且藏在深洞里,他本来可以在洞口时就捉住那只被他捉过了十来次的螃蟹,但他并不能集中精力。用余光看她使他不能专心捉蟹。
水里映出一个鬼魅一样的影子。他有些累,现在他想泄气了,但看到她坐在石板上微笑着——和第一次一起捉蟹时的微笑何其相似啊——等他。他又跟自己较起劲来。
他现在几乎把整个肩膀都塞至洞口了。与凸凹不平的石底磨擦使他的手酸痛不已。但是,与那次不同的是,他现在已触到那只顽逆的大蟹。它正挥动着它的武器,警告他:别碰我,别碰我,大爷没心情陪你玩。
他的手指与它的钳子交手了几次,仍未分胜负。他停下来,琢磨着它的壳在哪个位置。他决定一招将它生擒,他胸有成竹,把目光向她投去的一顺间手指向蟹壳扑去。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水面,他的手指扑了空。他轻轻地抖动中指,还是碰到了它的钳子。啊,他已经很久没被蛰过了。他没有想到会被如此大的钳子夹住,他先是感到钻心的痛,三四秒后感觉他的手指头已经不在了。他使劲咬着牙,他竭力使自己恢复平静的表情。他想在此刻看着她。
但他不能带着任何扭曲的表情看她。她的脸仍然淡漠。她看到他的表情依旧。她又想笑,但她仰着头思忖了一下,又打消了微笑的念头,他轻轻地往洞里塞手臂,蟹感到威胁正逐渐减小,况且它也累了。终于,它丢下手指头跑进他够不着的深洞里去了。他的手指在水中痉挛了两下,轻轻地取了出来。她笑了,又是哪种嘲弄的微笑。
渐渐地,血染红了水。她跳进水里,大踏步走到他身边。敏捷地举起他的手至眼前,她朝约有1厘米长的鲜红的口子吹了两口气,然后用自己纤细的手指头压住了那条醒目的口子。
“你很痛吧?”
“不,不算痛,这家伙太狡猾了。下次捉到绝不饶它。”他若无其事地说,并尽量使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滑稽一点。
“你今天的样子真像我第一天看你捉蟹的样子。”
“我不觉得,我很正常。”他并不想听她说这样的话,这会使他莫名地恼怒。
“我说说而已,其实你并不像,那时你细皮嫩肉,身子瘦弱。哪像今天这样长成一条不折不扣的牯牛。”他跟她说起过他喜欢牯牛,尽管她觉得一个瘦子喜欢牯牛显得很滑稽。他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挽着他上了岸。
她们坐在石板上,他要求她放开她的手指,她死活不肯,说还要再坚持会儿。他依了她,但觉得沉默着并不好受,便找话题聊开。
“今年的李子真让人失望,树枝上稀稀落落的就那么几颗。而且果子小,要是往年,枝头硕果累累,我爬树的兴致也会高一点。”
“都说瑞雪兆丰年嘛,你看去年这冬天像啥冬天。我都记不得是否穿过棉袄就过去了。”她乐呵呵地说,倚在他身边。
“去年冬天里的阳光太多了。我们都常到操场上打球呢。不是大家怕冷,实在是不冷的缘故。你看,今年年一过反倒冷起来了。雪下得少,冷冻得厉害。我看到鲜鲜的花苞都被冻蔫了。”
“今年的果子怕是下学期开学都成熟不了。”
“看样子这假期是吃不了了。开学后应该能吃了,不过下学期我可不想再给你带最好的李子了。我要你给我带。”
“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她。她也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沉默了。现在她丢开了他的手指,他现在反倒很不情愿她丢开,虽然伤口早已不疼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凝神静听蝉在包谷林或某棵树上发出的鸣叫。蝉声把他的记忆牵得老远。
他没想到,他身边这个女孩会和他同桌将近两年半。这些日子里,白天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一起渡过。学校里在一起。下午放学后也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割草、捞松毛,一起偷果子,她干什么都眼疾手快,动作麻利,和她一起无论是干活还是捉螃蟹或捉泥鳅之类的事,他都有一种安全感。她不会给你带来多少麻烦。她不是他的累赘,相反,她帮了他不少的忙。
他有一种对富贵人家天然的仇恨。他把这些人家的人想象得凶神恶皱,人面兽心,口密腹剑。他觉得是他们造成了穷人的贫困。当然,这种对富贵人家天然的仇恨多是针对长辈们,对于侪辈,他倒觉得无可厚非,但他对待这些侪辈却极为不恭,他常把他们当作纨绔子弟看待。
这种对富贵人家的鄙夷心理,使他在与她同桌后——面对她时有些尴尬。她的爷爷解放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解放初仍没有衰败下来,等到老头子死后,家道才一度衰落。但善于理财的妈妈和勤劳的木匠爸爸不久便重振家声。再加上遇上了天上掉馅饼——他们搬迁房屋至李昕家对面山埂上后拆了老篱笆房子,居然在壁缝间挖到一坛金子,从此他们又跻身当地最殷实的人家之列。
她的父母年过半百。她们六兄妹打小不愁吃穿,日子也过得平淡。父母明显地偏爱两个小儿子,但她们四姊妹也并不嫉恨两个小弟弟,相反,她们像父母一样对他们爱护有加。父母严格要求两个儿子,强迫他们努力学习。但两个儿子都不够争气,拿回来的成绩每每使父母失望。
至于女儿们,像平常人家一样,让她们自己决定。学习差也不责怪他们。毕竟,这一带还没有建立起女儿读书改变命运的理念。
她在四姊妹中是最小的一个,父母亲切地叫她“幺姑娘”。英子也知道父母很爱她。她看见他们提起她便由衷地微笑时,她便激动不已。当然,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她也不是读书的料。她的成绩从没考过班上前三十名。(那时每个班一般有五六十人)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父母常开玩笑地跟他们的幺姑娘说:“你就留在我们身边了,我们舍不得把你嫁出去。”
“行啊!”她欣喜地回答。她自己也很乐意留在这对相敬如宾的夫妻身边。他们心里却为她的终身大事操着心。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的三姐也在今年正月出嫁了。现在只剩下一个独姑娘,且是他们最疼爱的女儿,你说他们能不操心吗?
二
这一带绝大多数的姓氏都属于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们的祖先是明朝一位姓李的谏官,由于在一次进谏中不慎触怒龙颜,被贬到蛮荒地。他选择这块相对水草丰关、土地肥沃的土地安顿下来。后来成祖召他回朝也不没回去,朝廷大概觉得不回去也好,便不再敦促他回去了。
这块土地座落在深山丛林里,到今天已有近千户人家,这不能不说是祖先筚路蓝缕的功劳。村里对非本族人家抱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但那个最殷实的地主——英子的爷爷——这一带唯一的一户黄氏人家除外。想到她爷爷,人们的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
他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救济最贫困的人家,年年坚持独自一人去修路,不求回报地帮人家写春联。他甚至还算个业余的星相士。很多人家都请他算过命,这些让他在村里威望很高,是名副其实的年高德劭的乡绅贤达。所以,即使解放后大多地主都遭了殃,成天遭群众批斗,黄氏一家除了损失了些钱财和土地,地位仍归然不动,村里人还是照样尊重他。可惜香港刚回归不到一年,他给李昕算命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作古了。
李昕仍记得母亲请她爷爷给儿子算命的事。这黄髯飘须,穿一身清末时代的灰色长袍的老者眯着眼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此子有福,定将驶向前方。”那时李昕刚上二年级。他傻傻地望着老先生,显然被老先生的话搞蒙了。虽然听不懂老先生说的话,但他从老先生语重心长的说话声中感到了一种肃穆得说不出的氛围。
后来老头子与母亲嘀咕了一阵,便神秘兮兮地向母子俩告别了。母亲看着他的背景消失在夜中,转过身来抚摸着小李昕的头。他却感到不好意思,小脸泛起红晕。他在心理说,妈妈,这老头跟你瞎嚷了些什么,都不让我知道。你再不说我就不理你啦。
“妈妈,我要睡了。”他没想到妈妈并不留他在她身边,这个矮小的女人点点头。他烦恼至极,又有些后悔没留在母亲身边。“什么叫驶向前方?”他在心里问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答案。
至那以后,父母在生活上更加关爱他。也开始跟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小李昕听着母亲讲的大道理,似懂非懂。这让他苦恼,但更爱母亲了。他觉得这时母亲更可爱,和他一样是个孩子。
尽管母亲千叨万絮地给他讲他应该如何勤恳,如何做到礼貌待人,如何学会独立自强……但这些并没有使小李昕有多少改变,他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听后便忘。他不可能将这些话铭记于心,他觉得她是让他摘天上的星星,怎么能摘到呢?
他记起老头出丧那天的情景,那是个亮堂但太阳被锁进云层的日子。差不多整个村子的人都流了泪,有些人悲痛欲绝。特别是女人们,多哭得死去活来,跪在地上不断用拳头捶打土地。出丧的队伍像一条长龙在山间蜿蜒,大人们相互挽着,他们一时无法从死去老大的悲痛中解脱开来。
但大人们的悲伤并不能感染孩子们的心灵。他们找不到悲伤的理由。不就是死了吗?并且已经活了七八十年,活着还不是个累赘?李昕也这样想。不过他并太像其他孩子一样忙着去捡还没炸的已放的鞭炮。他跟在披麻戴孝的人们身后。他对于大人们小题大的出丧很是不屑。他为看热闹而来,开始他和母亲一起走在出丧队伍前面,由于受不了母亲的嚎声大哭,便跑到了后面来。
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英子。她身穿缟素。一声不吭地跟在大人们后面,她并不悲伤,为了附和悲伤的氛围,她不得不阴沉着脸。但她使劲眨了几次眼睛都挤不出泪水来,也就泄气了。他并不知道她就是英子,他也懒得去理她,他一直生活在别处。
直到她眼圈都哭黑的母亲跑来叫她到队伍前面拿他爷爷的相框时,他才知道这个村里有个叫英子的姑娘。但他只睃过她两眼,没有深刻的印象。唯一觉得她特别的地方是她那双鼓鼓的水晶般的大眼睛。但他对这次出丧大失所望的心理使他在老人还没下葬就溜了。
他本来可以更早认识英子。但他沉默寡言、不爱走家串户的脾性,使得村子里很多同龄人他都不认识。他更是不想了解殷实人家的情况。
英子在这一带也算得上大家闺秀。这些日子她把她的野性都压在骨子里,只在她童年的屋子里玩耍。他们家隔得不算远,但这四五公里路的距离已经不再他走家串户的范围了。(当然,要是他们在二年级时就在同一班的话,他们也会认识的。但英子是在四年级才从另一间公立学校转过来的)
后来他觉得那时他们就像两个快挨在一起脸却朝向相反方向的人。一转身就可以发现对方。但大家都抒矜持着不愿转过身。不过他相信,他们是注定会认识的,不可能不认识。他觉得即使不曾见面,他也会梦见她。
确实,在他们第一次一起捉蟹之前,他的梦是浑浑噩噩,模糊不清的。他只能在梦中听见两个人的脚步声和一个模糊的女孩的身影。偶尔他也能听到淙淙流水的声音,林子或草地被触碰发出的窸窣声。后来他发现那个女孩的影子就是她。可他想起来又觉得可笑,他觉得她是悄悄地涉入他的梦境的,而他太过漫不经心。他想象着要是这几年没有她的情形,便不免心惊肉跳……
他回过神来看着她,觉得她的面孔有点陌生。他注意到了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蚊冲向她的脸飞奔而来。他的手在她眼前闪了一下,蚊冲已被握在手里。他摊开手,蚊冲扎挣着飞走了。手掌有一根蚊冲的腿足。“你真该把家伙捏死。”她笑着说。又沉默
下一篇:宝贝谢谢你曾来过

 SEO优化
SEO优化  自媒体
自媒体  电商运营
电商运营  文案软文
文案软文  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  模版资源
模版资源  行业观察
行业观察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